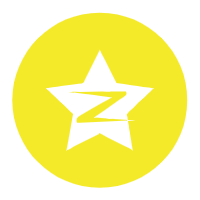編者按:
為進一步提高青少年的生態文明意識與科學素養,激發青少年投身美麗中國建設的積極性,有效提升公眾生態環境意識,2025年,在湖南省生態環境廳的指導下,湖南省生態環境事務中心開展了“美麗中國,我是行動者”綠色衛士下三湘主題實踐活動暨“世界讀書日”征文活動。活動共征集到作品2400余篇,作者們結合自身環保實踐及身邊事例,以細膩的筆觸表達了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美麗中國建設的深刻感悟,情感真切,富有深度,現對部分優秀作品予以展示。
成人組
山林之魂
文/鄧旭剛(湖南省工程地質礦山地質調查監測所)
村東面的梯田止于兩座山的山腳。兩座山就像兩條鯉魚,首連首,尾連尾,把中間圍成了一片地勢低洼卻很平坦的盆地,整個盆地面積約莫百畝,全是沃土和良田。爬上“魚尾”之前,建議你先做好心理建設,因為山脊線這邊是陡坡,那邊卻是上百米高的懸崖絕壁。“魚頭”這邊,山腰以下是大小高低不一的石頭,所以左邊的山叫“石嶺上”。右邊的山面積稍大一些,山嶺也高一些,尾尾相連的地方,有一個大溶洞(我們這稱溶洞為“坦”),有盆地有坦有嶺,所以右邊的山就叫“坦盆嶺”。兩座山的石縫里長滿荊棘和低矮的灌木叢,想從這里進山非常困難。進山要從兩個“魚頭”的中間地帶直往盆地沖,入口處依地勢筑有三個山塘,過了三個山塘,各條上山的羊腸小路便分布在“魚腹”“魚尾”各處。
山腰以上才是這兩座山土厚地肥之處。山中自然生長著眾多質地堅韌的雜木,苦櫧樹尤為繁茂,楓樹、樟樹、櫸樹、柏樹、野梨樹、松樹、杉樹等競相生長,其間還夾雜著一些我不認識的樹種,共同構成了這片繁茂的森林。大伯曾言,這兩座山與村子的風水息息相關,自先祖遷居此地,便立下規矩,禁止隨意砍伐,故而它們成為村里的禁山,世代守護。
大伯就是這兩座山的護林員。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我上小學、初中的時候,跟隨大伯巡山是我最快樂的事。一來大伯不會老在我耳邊嘮叨“好好學習,將來做個有出息的人”;二來山上物產頗豐,是個大寶庫,上山就有驚喜收獲。一到假日,爸媽在家中呼喚我兩聲,未見回應,便喃喃自語:“唉,這小子又跟著大伯去山里瘋了,這樣下去,將來怎能有出息!”這時候我已爬上了一棵枝杈野蠻生長的大樟樹,準備掏鳥窩,鳥媽媽在樹梢上驚慌失措地跳躍,向我哀求似的叫喚著。樹下,大伯喊著我的名字,我卻裝沒聽見。大黃仰著狗頭沖我“汪汪”叫。既然它的主人是大伯,那么此時出賣我就是它的分內之事。大伯不緊不慢地說:“好哇,跟你說過多少次不要爬樹,一會兒沒看住就上樹了。萬一被你爸媽知道了,打你事小,還會連我一起挨批!”
幾束稀稀拉拉的陽光從茂密的葉縫中穿過,忽閃忽閃地打在大伯的臉上,更顯得他的皮膚黝黑發亮。我央求道:“大伯,這鳥窩里的鳥蛋拿回去給你吃,求你別告訴我爸媽!”他語重心長地說:“鳥窩是鳥兒們的家,鳥蛋是鳥兒將來的孩子,誰動它們,我就跟誰急……你聽,鳥媽媽看你要掏鳥窩,叫聲多慘啊!”這時再聽鳥叫,急切且悲哀。人性本善,如此這般,我便乖乖地從樹上下來了。
大伯離開的這會兒,抓來十來條長相跟蠶相似的蟲子,個頭比蠶大一些,用一個玻璃質地的橘子罐頭瓶裝著,胖嘟嘟的,挺嚇人。他搖晃著罐頭瓶,湊近我眼前,眉頭一皺,那本就布滿皺紋的臉龐,此刻更像是一幅交錯的溝壑圖,深深淺淺地刻寫著歲月的痕跡與一生的滄桑。他說話慢條斯理,不急不躁:“看你老爬樹,而且還做壞事,這么美味的東西真不想給你吃。又看你知錯能改,就功過相抵吧。記住了,以后不準上樹,尤其要愛護鳥類!”我點點頭,又指著罐頭瓶搖頭,雙手捂嘴表示惡心,卻忍不住笑出聲,堅信大伯在戲謔我,心想這么可怕的蟲子怎么能吃。大伯說:“等會兒香死你!”
我們直奔溶洞。大黃跑在前,保持著狗狗該有的警覺。但凡它突然站住不動,立耳凝神,鼻子翕動,身體繃緊,尾巴下落,那肯定有情況。這不,大黃堅定地停下了腳步,變得嚴肅起來,在我們還沒有任何異常感知的時候,它已經毫不遲疑地離開道路沖進密林。大伯一邊喊“大黃,慢點!”一邊對我說:“趕緊追,除了老鼠,不準大黃咬其他的動物。”
狗在密林里奔跑,一眨眼就不知了去向。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聽到大黃狂吠的聲音和一個男人向我們大聲求救的聲音:“老哥,快來救我,你的狗要咬我啦!”我們吭哧吭哧趕上去一看,好家伙,一個大叔正在一棵苦櫧樹上,手拿柴刀,刀落之處的枝杈幾乎就要砍斷。大黃在樹下狂吠不止,屢次躍起欲咬大叔腳后跟,卻總是差之毫厘,直至大伯一聲令下,它才安靜下來。
鎮定下來的大叔滿臉歉意地解釋:“老哥,我……我只是砍一個小樹枝拿回去做鋤頭把!你看,這么小的樹枝而已,剛好是鋤頭把的大小。”
大伯曾經說過:“大黃就是我的好幫手,有它在身邊,什么都不怕。”從他臉上洋溢出的自豪與驕傲中,不難看出,大黃如同他的親人和摯友,更是他的守護神。誰說不是?那時大伯母已經去世了十幾年,子女們都已成家,平時基本與大黃為伴,所以大黃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溶洞冬暖夏涼,附近干活的人常來這里休息,算是整個“鯉魚”體系的中心。洞里沒人的時候,遠遠地可以看到動物們站在泉邊一邊喝水一邊警覺地四處張望,我們走近了就一哄而散。洞口很大,目測高度有十幾米,洞底與“盆底”一致,遠看就像是山體開了一扇黑洞洞的大門。洞前有一汪從未斷流的清泉,泉水流入洞內的石縫后便不知所終。泉邊有一片沼澤,上面長滿了野芋頭。忘戴草帽的人過來摘一片大的芋頭葉戴在頭上遮陽,順便摘一片芋頭葉打一包水帶走給別人喝。洞內越往里走地勢越高,最高處幾乎到了洞口高度的一半,也是在最高處,洞頂突然開了個直徑八九米的漏斗形天窗,天窗下面有個洞中洞,小洞向下橫穿整個“魚尾”,里面漆黑,彎腰可入,曲曲折折,百十來米后就到了山那邊的絕壁之上,甚是恐懼。
大伯把斜挎帆布包取下放在洞口石頭上。帆布包是村里配的工作包,本色是白的,歲月閑來無事,幫著給包染了個黑黃色。別人提醒他該換包了,他指著自己身上滿是補丁的、洗得泛白的軍綠色衣服說:“衣服縫縫補補都可以穿,要那么新的包干嗎?”每年的新包,他都送給村里上學的娃娃當書包了。
大伯把帆布包打開,里面露出一把柴刀,一把鐮刀,一桿短煙斗和一包旱煙絲,還有一個小一號的銅鑼。作為護林員帶些刀具可以理解,帶個銅鑼?這玩意天天放包里,挺沉,卻很少用到。你不覺得費勁,我卻感到困惑!這里,大伯對我進行了科普。銅鑼有三種操作模式:一是連續不斷地敲打,表示有人偷樹;二是連敲兩下,間斷一秒再敲兩下,反復操作表示失火;三是連敲三下,間斷一秒再敲三下,反復操作表示遭遇野獸,當然通常這種情況下野獸就基本嚇跑了。一旦銅鑼一響,村里人就會第一時間循著聲音趕過來幫忙處理。妥妥的森林報警系統嘛!
在洞里,大伯準是先拿出煙斗吞云吐霧一番。身為護林員,他堅持以身作則,絕不在山上吸煙,也不允許別人在山上吸煙,所以,大伯已經忍了一整個上午的煙癮。他說:“想要禁止別人,先要禁止自己!”我被旱煙嗆得連連咳嗽,大伯笑得露出被旱煙長期熏成黑色的牙齒說:“你拿帆布包里的紅薯干和花生去一邊吃吧。別光顧著自己吃,給大黃吃點!”大伯親自晾曬的紅薯干脆甜脆甜的,這是我和大黃都喜歡吃的零食。
大伯抽完煙,便去外面找些柴草來點燃,然后把罐頭瓶里面的蟲子放火堆里煨,蟲子撲騰一下就死了。大伯凝視著蟲子,苦笑著說:“最近你們真是囂張至極,把我們的樹都蛀空了,害得我不得不親自出手。既然我費了這么大勁才抓住你們,那不吃掉你們豈不是太可惜了!”
一會兒,蟲子就熟了。大伯用兩根小棍子做的筷子,將烤得焦黃的蟲子一條條夾至芋頭葉上,用那雙布滿厚繭、粗糙如石的手,小心翼翼地捧著葉子,一邊抖動一邊對著吹氣,幾經反復,蟲子身上的草木灰便褪去,這時大伯示意我可以享用美食了。即便大伯如何慫恿我享用“美食”,我卻保持著無法撼動的立場。大伯萬般無奈,獨自吃得津津有味,我看得目瞪口呆。
我曾經以為,或許是時代的原因,貧窮的人逮啥吃啥,但另一些事證明,我的理解有偏差。
有一次,大黃發現一只山雞被困在人工陷阱里,正焦急得上躥下跳。大伯頓時怒不可遏,對著山谷大吼:“你們這都是什么人啊,先用氣槍射鳥,再換彈弓打,如今又設陷阱,讓我這老頭子如何把山里的蟲子捉盡?”大伯毫不猶豫地把明明已經到嘴的野味當場放生,可見大伯并不是饑不擇食的人。
山里也有大伯索取的東西。除了樹蟲,野果、草藥、蘑菇以及各種野菜都是他眼里的寶。苦櫧成熟的時候,他會采回家一些做成苦櫧豆腐。這玩意談不上好吃,但據說當年它曾幫助人們熬過饑荒立下了汗馬功勞。石嶺上的馬齒莧是大伯的萬能藥,被大伯廣泛用于止血、退燒、止瀉以及蚊蟲叮咬等問題。楓樹嫩葉被大伯采回曬干,整個夏天他就喝楓葉茶。草藥是大伯眼里最有價值的東西,我還記得破石珠、雷公藤、苦參、石上柏、梔子、土茯苓等幾味草藥。采草藥必須在他的親自指導下進行,他遵循的原則是:幼苗不采,成熟者需留些許根莖以續其繁衍。就連挖野菜時亦需留種,否則日后便無以為繼。山里的野果子是屬于孩子們的寶,有柿子、山楂、八月炸、金櫻子、野葡萄、樹莓。大伯要求我摘野果的時候要專門給鳥兒們留一些——事實是,多數情況下,我們能夠吃上的野果都是鳥兒們留給我們的……
大伯也有討厭的“東西”。他說:“我看到狩獵者比看到老鼠還難受!”狩獵者就是他所說的“東西”。那段時間,農村盛行捕獵,比如抓蛇,有人以此謀生,有人以此為樂,有人以此為食。生靈涂炭,野生動物逐年減少,當地穿山甲、獐、麂、狐貍、野豬等動物就在那個時期絕種了。老鼠卻因為蛇類銳減,沒有了天敵而大量繁殖,導致莊稼連年歉收。有人投放老鼠藥,卻不承想,毒死了老鼠也毒死了不少野鴨、山雞及其他鳥族,可謂殺敵一千損友八百。大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從此杠上了那伙捕獵者,多次發生口角。捕獵者說:“當初野豬肆虐,這老頭求著我們打,現在連只兔子都不準打。”大伯硬氣地回應:“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這山里的東西什么能打什么不能打我說了算!”后來,大伯這個年近古稀的老人放話為了保護動物要和捕獵者以命相搏,捕獵者才放棄這片山林。
他們的放棄或許有大伯的原因,或許是他們所需的資源已經匱乏了。那段時間應該是大伯的至暗時刻。他從人民公社成立不久就當上了護林員,長期的工作經驗告訴他,護林并不是單一保護樹木的工作,而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地維護生態平衡的工程。可是他辛辛苦苦維系了幾十年的生態平衡被這些捕獵者毀于一旦,心里的痛苦難以形容!大伯坐在溶洞的石板上,背靠著巖壁,左手握著煙桿,右手撫摸著挨坐在身邊的大黃的腦袋,仰望山巒,神情沮喪,喃喃自語:“大黃都知道除了老鼠,其他的動物都不抓,為什么人卻還不如狗這么懂事呢?”
那些日子,大黃的伙食得到極大改善,幾乎餐餐有肉,先人一步過上了小康生活,再也不用啃人丟棄的骨頭,更不用去和別的狗為了一坨熱乎乎的??去打架了。大伯訓練大黃抓老鼠,把抓到的老鼠褪掉皮,去掉內臟,然后用鐵絲串起來架火上烤熟給大黃吃。別說,那香味飄來,連我都流口水。大黃抓老鼠更加賣力,越發長得膘肥體壯。大伯對著大黃“嘿嘿”一笑:“真沒想到,最后得到便宜的是你這個畜生!”
中午,我們會在洞里小憩一會兒。此時,只聞野鴨田間啄食之聲,竹雞求偶之鳴,其余聲響,幾近于無。偶爾有一兩只翠鳥可能在山塘沒捕到食物,便來到野芋頭間的水溝里啄蝦。最熱鬧的場景無非是一群麻雀歡快地在枝頭跳躍,開心聊著天。當然最動聽的是布谷鳥空靈的叫聲,響徹整個山谷,在盆地里回蕩。山風輕拂,美妙的樂章在耳邊縈繞,這大概就是大自然最誠摯的饋贈吧。閉上眼,大伯就睡著了。我睡不著,確切地說是不敢睡。我怕野獸,更怕蛇。直到大伯醒來,問清我不睡的原因之后呵呵一笑,說我太不信任大黃,說他還有護身符。然后他拽過來一個掛在他腰間的小布囊晃了晃說:“這里面有幾種草藥,帶在身上,蛇蟲不敢近身!”此后,我還是不敢在洞里睡覺!
秋收以后,水田里只剩稻茬,大伯就帶我下田抓泥鰍和黃鱔。水田的泥很深,有的地方一腳下去就沒過我的膝蓋,行走很吃力。我根本抓不到泥鰍和黃鱔,但撿到很多田螺和蚌殼。大伯把抓到的泥鰍和黃鱔用一根粗壯的狗尾草從鰓部穿過嘴巴把它們串起來,讓我提在手上。晚上就在他家打平伙,酸辣椒炒泥鰍那個味道,至今難忘。
最后一次陪大伯巡山,發生了意外。
那天下午異常悶熱,天昏地暗,雷電交加,很快下來瓢潑大雨。我們躲在空蕩蕩的大溶洞里,面對大自然那震耳欲聾的咆哮,我渾身顫抖,雷聲仿佛就在頭頂炸響,讓我深刻體會到了“如雷貫耳”的真正含義。大伯難以置信地說:“都快中秋了,竟然還有這么壞的天氣,難道是人們觸怒天神了嗎?”大伯帶著我往里走,不準打赤腳,不準坐地上,也不準靠巖壁,還不準我張嘴。聽多了大伯講的關于妖魔鬼怪的故事,我清楚地記得妖怪也住在洞里,我還記得他說過老天收拾妖怪就是在妖怪張開嘴巴的時候放電給妖怪吸進去。此時,我感覺空氣凝固了,頭腦嗡嗡作響。我們站在洞穴深處,緊閉雙唇,一動也不敢動,生怕雷公電母找錯了目標,那種充斥著整個身體每一個毛孔和每一根神經的恐懼,讓我感受到小心臟就在喉嚨眼撲通撲通地跳動著,極度窒息。大伯意識到我的恐懼,他大概也是鼓足了勇氣,電閃雷鳴那一剎,大伯連聲安慰我時一張一翕的嘴巴更讓我增加了幾分擔憂。
突然,大黃顯得不安起來,伸著脖子探著頭朝著山塘方向狂叫,不大一會兒,山塘方向的洪水像猛獸一樣轟隆隆沖過來。大伯再也顧不上該不該閉嘴,惶恐地重復:“不好,山塘決堤了!山塘決堤了!”開始,所有匯聚過來的水都能從泉水流走的地方消掉,后來,水量太大,不一會兒洞內和整個盆地成了一片汪洋,里面那直通懸崖的小洞,竟成了泄洪口。虧了這個小洞,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就在以為洪水對我們構不成安全威脅的時候,還是出了問題,被洪水沖刷過來的枝枝葉葉竟然堵住了泄洪的洞口。眼看水位漸高,大伯趕緊從水里撿來一根樹枝,努力探出手試圖用樹枝撥開堵塞物,但距離太遠,效果不大。危急之時,大黃“撲通”一聲跳入水中,竭力將枝枝杈杈移開,十來個回合下來,洪道突然打開,大黃被猝不及防的洪水強大的吸力猛然吸走,可憐的大黃連回頭看主人最后一眼的機會都沒有就消失不見。
此后,夕陽下,大黃跑在前面,不時回頭望望我們,眼中滿是歡喜的情景再也沒出現過。
也就是這個時候,大伯結束了護林員生涯。離開山林的大伯如同失了魂、落了魄,終日無所適從。白天,村里好像突然多了一個老人,他胡子拉碴、頭發花白、個子精瘦、佝僂著腰,握著一根煙桿的雙手時常反剪在背后,步履緩慢又懶散地在村里踱來踱去,偶爾聽到他回頭大喊一聲:“大黃,跟我回家!”
夕陽如血,將一道孤寂的人影拉得老長,從村邊投至梯田的盡頭,最終定格在坦盆嶺的樹梢之上。那背影,宛如一幅凄美的畫卷,透著無盡的落寞,又似乎在追尋著逝去的記憶,卻深知那些美好已如流水般逝去,再也無法觸及。
1998年臘月,大伯離世。按照他生前遺愿,他葬在了坦盆嶺山腰。
總策劃 :唐 宇
主編: 謝可軍 蔡宇華 舒麗娟 彭 勃
編輯 :楊 菲 陶 佳 劉文馨 李 巍 陳 鳳
美術編輯 :陳思思 陳秀平 章楊梓昕
校對 :傅衛鋒